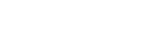闻效仪认为 , 零工经济实并非像其宣称的那样“高薪”“自由” 。 “高薪”来自于逃避的社保成本 , “自由”则只有“抢单自由” , 骑手并没有“工作自由” 。 “对于高技术人群来说 , 灵活就业可以让他们在两三个月赚够一年的钱 , 他们是主动自由;而对于骑手、家政等低技能劳动力来说 , 他们需要每周至少工作6天来保证收入 , 实际上是一种被动自由 。 ”
“零工经济的本质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经济 。 ”闻效仪说 , 在需求大幅增长的背景下 , 如何保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 , 平台在其中起到大规模的组织作用 , 并介入到对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中 。
“由于全部劳动过程的数据可留痕 , 平台对劳动过程的监控会更严密 , 劳动者所受到的指挥和控制也会更多 , 相应带来的压迫感也会更强 。 ”闻效仪认为 , 劳动者也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 。 例如评价体系已经是劳动者标注在个人身上的固定资产 , 需要通过不断的好评来形成个人名誉资产的增值 。
2020年6月13日 , 重庆市的一名代驾人员(左) , 带着体验代驾工作的儿子在深夜一起回家 。 图/IC
劳动关系难认定“平台零工作为新的、复杂的用工形态 , 相应的研究和规则制定相对滞后 。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姚艳姣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这导致了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模糊、平台权责不一等乱象 。 ”
在致诚的研究中 , 需要维护自身权益的骑手甚至难以找到用人单位 , 无法确立劳动关系 。 外卖平台与大量配送商正是借此操作在不同程度上逃脱了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 。
为何会无法认定劳动关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平台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上 , 在前端和后端都有相应的规则来处理 。 前端是在立法层面 , 如果劳动者与平台签了劳动合同 , 意味着在前端就直接被纳入到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内 , 平台跟劳动者的关系就适用劳动法的规则来调整 。 即便前端没签劳动合同 , 但在实际用工过程中 , 平台对劳动者的管理和控制是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的 , 那么在司法过程中也可以认定构成劳动关系 。
此前 , 2016年7月 , 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 , 网约车平台公司“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 , 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 。
“这意味着之前政策开了一个口子 , 如果可以签劳动合同 , 也可以签非劳动合同 , 企业可能就没有动力遵循更加正式的劳动关系 。 ”范围说 , 后端在司法裁判的层面 , 对于法律关系定性 , 司法态度较为保守 。
目前专送骑手劳动关系认定比例(“认劳率”)很低 , 根据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研究 , 外卖平台的认劳率基本控制在1%以内 , 配送商的认劳率也仅为46.89%和58.62% 。 此外 , 复杂用工模式下骑手劳动权益被 “区别对待” , 法院开始视“场景”严重程度(人身损害抑或财产损害;伤残等级等)决定是否认定劳动关系 , 工伤案件的认劳率明显高于工作报酬或社保纠纷案件的认劳率 。
这一难题在去年迎来了转变 。 2021年7月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家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平台用工形态进行了初步划分 , 将新业态劳动者分为“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三种类型 , 保障程度与依据不尽相同 。 对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 , 要求各地指导平台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 , 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
不同学者对于是否需要认定劳动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 。 孙萍认为 , 由于社保机制的困扰 , 为了更快地解决痛点问题 , 可以绕开劳动关系谈社会保障 , “比如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 我们先解决最痛的点 , 漏洞先堵一个算一个” 。
闻效仪则认为 , 劳动关系是就是 , 不是就不是 。 “它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 , 不代表它不是劳动关系 , 它可能只是劳动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 。 例如现有法律制度里面的非全日用工劳动关系 , 仍然覆盖在劳动关系中 , 需要符合最低工资标准 , 同时上工伤保险 。 ”
回到现实中 , 困扰依然存在 。 姚艳姣说 , 根据《指导意见》 , 外卖行业的专送骑手不是来去自由的“平台零工” , 而是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 , 众包骑手则大多属于“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 。 范围认为 , 至少双方的关系要回到“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 , 但实践层面 , 这个规制可能会被平台的策略架空 , 变成仍然没有劳动关系的状态 。